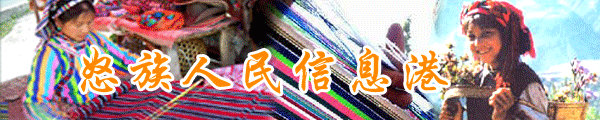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怒族的文化传承
怒族的学校教育直至20世纪初才在政府的帮助下得以产生,而自古以来,由于怒族先民没有文字,怒族的历史文化均靠口耳相传,代代不息,甚至到了本世纪中期还有少数怒胞过着“刻木记事,结绳记时”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光辉下,怒族的教育事业掀开了全新的一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怒族同胞人才辈出,不仅已有800多名怒族干部相继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而且还逐步造就出怒族人民的教育、文化、卫生、科技、交通、邮政、商贸、部队等行业的工作者,怒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第一节 民族教育发展
对人类社会而言,不管其社会形态高低,都必须通过教育来为其物质、精神及人的再生产服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的最基本的途径是家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逃脱其从儿时所处环境中所获得的那种文化的影响;或者完全超越这一文化层次。因此,要了解怒族教育及传承的发展史,就必须追溯怒族的原始教育。
一、原始教育的产生及场所
怒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设法确保物质再生产及人的再生产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对每个原始民族来说都是非常可贵的财富。一个新生命的降生,无疑为部落氏族又带来了一线希望。为了使这个新成员向着怒族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他们也需要教育来向孩子传授使用和制造生产工具的方法;了解并形成特定的行为习惯,掌握并遵守特定的道德规范,学会团结互助、进行集体的采集、狩猎及刀耕火种的劳动技能,熟练地掌握与毒蛇猛兽及其他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方法,增强部落意识,了解民族历史,提高抵抗外族侵犯的能力。总之,怒族也需要教育来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怒族的原始教育正是在这种最基本的需要之下,自然产生的。
历史上由于怒族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他们不得不采取群居的方式,利用氏族集体力量和毒蛇猛兽及险恶的自然灾害、人为灾害作斗争。怒族处于氏族公社时期时,一个氏族便是一个部落。地域观念及私有观念出现以后,各氏族间按照山岭、河谷、溪流、森林等自然环境来划分各氏族间的区域、领地,互不侵犯。
为求得生存,每个氏族成员都必须与氏族保持高度的一致,才能确保个体及氏族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成果。具体地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祸福就是氏族的祸福,氏族的祸福也是每个成员的祸福。两者的命运没有哪个社会联系得如此紧密,甚至可以说成员与氏族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父母、兄长、亲友、同伴、氏族成员等都可以充当教育者的角色。这是一个“能者为师”的社会。换言之,就是说,每个氏族成员对后代的教育都负有责任。
从形式上看,怒族早期的教育活动大多是在集体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进行的。整个教育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相联。其主要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掌握集体生产和生活的技能,能动地遵守氏族社会的行为规范,为氏族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障。从广泛意义上讲,怒族的整个生活空间,都是教育后代的场所,生产及生活内容的全部便是教育后代的内容。从个体家庭的角度来看,“火塘”就是怒族早期教育的场所,一个人的童年的大部分要在这里度过。同时“火塘’’还是人们学习生活知识、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怒族许多重大的事件都与火塘有关。像氏族历史类的歌都要在火塘边唱,怒族还将这类歌称为在“火塘边坐唱的歌”。正是这些歌使每个成员对本氏族、家族的历史有了了解。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怒族还有一个特定的,富有特色的教育场所——“哦吆” [①] 关于哦吆的来历,段伶说有的是父母为儿子盖的,有的是寡妇或孤儿的住房,有的是主人远行或去世留下的,总之村村都有。旧时,当孩子长到十来岁后,就要离开父母,到“哦吆”里寄宿。他们在那里学弹琵琶,学跳舞,制弩削箭,捻麻绕线,玩耍取乐。哦吆是造就少男少女们性格、气质、技艺、社交能力的公共场所。当孩子们进入恋爱期后,这里又成了他们谈情说爱的场所。从这个房子的功能来看,它事实上是氏族社会为每个尚未成年而又将进入成年阶段的成员准备的一种“自修式”的教育场所。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好今后作为成年人应具备的生产生活技能。换言之,哦吆事实上是怒族青少年进入成年行列的一个资格训练所。而这个资格是以自学的方法获得的。 从某种角度上说,怒族教育其实就是原始的“生活教育”。其内容涵盖了氏族生活的全部,各种教育之间交替地进行。
对任何一个原始而封闭的民族来说,生产、生活的经验能否代代相传,它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的人文经验、生产技能及各种经验的再生产活动,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它直接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经验是每个原始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如一个民族不能有效地将上代的生产、生活经验承接下来,并把其有效地传给后代,其后果不堪设想。在一个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中,他们只有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来进行文化的传播,其中口耳相传的形式又更为重要为了确保经验不致很快地失传,这些原始民族便创造出了民间文学这一形式。原始的先民们将他们的智慧结晶、人生观、世界观、行为准则等内容有效地纳人到各自的神话传说、寓言、童话、笑话、歌谣、叙事诗、谚语、谜语、歇后语及曲艺等之中。这些生产、生活经验由于有了这些民间文学形式,为它提供了信息载体,并给它赋予了更形象、生动及趣味的特性。怒族甚至还把一些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经验神秘化,迫使后人深信不疑。这种创造性的活动,无疑加大了生产及生活的信息量。因此,怒族即使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之下,也能将其祖先的生产、生活经验及文化历史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②]。 二、怒族的近现代教育
(一)怒族解放前的教育
怒族地区因设治太晚,经兼办怒俅两江事宜的夏瑚的再三请求,清政府才批准他于1910年在贡山的茨开及菖莆桶两地办起了两所汉语学堂。其目的是要“开化夷民,使边夷人民逐步学会汉语,掌握初等文化并且有一定的爱国素质,巩固边防。”这两所学堂的创办,在怒族地区拉开了学校教育的序幕。
民国时期,兰坪改州为县,泸水、碧江、福贡、贡山也相继设治,随之创办新学也在各县逐渐展开。兰坪于民国2年(1913年)开始筹建小学,到民国8年(1919年)先后开设了官立高等小学3所、私立国民小学53所,学生达1351人。1912年,李根源奉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之令,命人在怒江地区建起了最早的县级编制——“殖边公署”(后称设治局),怒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才小有发展。由于怒地地瘠民贫,政府财力匮乏,特别是1921年后的内战不息,社会动荡不安,金融秩序日趋混乱,粮饷浩繁,百业皆废,使怒地难于找到教育经费。加之师资奇缺,学校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室内除几张课桌椅及黑板外,“余则四壁”,师生生活苦不堪言……凡此种种的原因使得怒族地区的学校时办时停,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实际上,在这段时期内只有极数怒族学生进过校园。
1931年的“土民教育”及1935年的“苗民教育”计划在怒江实施。1936年省立碧江小学还招收到了4名女生,从而结束了怒族女孩不上学之历史。当年,仅贡山、福贡两县就开办了18所小学。其目的是要“推广土民教育,唤醒土民之觉悟和素质,增强国防力量。”1937年,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后,政府紧缩了对教育的投入。1940年,受抗战影响,云南不能再进口外烟,特捐收入锐减,教育经费的来源枯绝,学校教育陷入困境。特别是当战火烧到怒江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更少了,不少学校因此而相继关闭。
1945年,内战爆发,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战争,不但将云南的卷烟捐收归中央管理,最后甚至还把办教育的责任全都丢给了地方政府。这对怒族地区来说雪上加霜。民国末期,学校因经费紧张而关的关,停的停,贡山县仅有的4所学校则因此而全部停办。
1950年9月13日,福贡县第一任县长李世荣在向中央民族访问团汇报时说:“在旧政府时期,福贡曾办过汉语学校、简易师范、省立小学,但完全都失败了。傈僳、怒苏把受教育和对服国民党的兵役一样看待。30多年来只培养出7个人,其中一二个人稍可做事,其余都赶不上内地4年级学生的程度,这就是解放前福贡的教育史。”上述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贡山、泸水、碧江的情况。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热心于怒族地区教育的教师也是有的。几乎每位省小教师在就职前都有要振兴怒地教育的雄心壮志。不少老师和校长甚至还“携眷而往”。这些教师中也确有惜才如命,想为怒族同胞多育人才者。如省立碧江小学的第三任校长李公治在被迫离任时,便把怒族学生胡汝英带到家中(永胜县)继续培养,后来将胡汝英培养成怒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再如大理州鹤庆籍的段重槐在离任时也将怒族学生窦桂生带回到老家,结果也将其培养成怒族的知名人士。这些在生活上自身难保的教师,尚能自费为怒族同胞培养人才,其精神堪称伟大。
从教材及教学内容上看:1910~1930年这段时问,汉语学堂所使用的教材很混乱,没有统一的教材。贡山、泸水、碧江自编的《汉语教材》供应正常时,学校一般都选择此种教材。否则,教师们只好找到什么书就用什么书去教学生,如《三字经》、《幼学》等则常常成了代用教材。对于这些书,就连当时的老师都搞不懂,学生则是整天都念而不知其意。相对而言,贡山、泸水、碧江的自编《汉语教材》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它采用傈僳话音(译)与汉语相对照的方式编写而成,而傈僳话几乎又是怒地的公用语言。因此,此种教材易教易学。如“米乃叫做地。”其中“米乃”是傈僳语的读音,意为“地”。
1930年后,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的指示,怒江的初级小学一律改用《短期小学课本》。按规定,汉语学堂只开设汉语课;短期小学、初级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体育、音乐、习字、汉语、会话。省小开设的有国文、算术、公民、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此外,高小还开设过“民众课”。抗日战争时期,体育课被改为了“军事体育”。由于统编教材不考虑怒地的实际,所以这里的师生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如因当时无铃上课下课全由老师指挥。要上课时,老师用手指教室高叫:“上课了,进去!”学生因不知其意也跟着叫:“上课了,进去!”老师喊“起立!”学生也叫“起立!”学生们只是跟着老师叫,却站着、坐着不动!搞得老师哭笑不得!这样的教材,这样的教师怎能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
除历史、环境、交通、管理、教师、教材等因素外,阻碍怒族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有教育经费及教学设备方面的问题。民国时期,怒江的时局一直动荡不安,战乱匪患及自然灾害一直困扰着怒江人民。受此影响,怒江的教育经费一直都没有保障,从而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学生虽名为享受公费待遇,但生活却极为艰辛。平时他们只能靠稀饭度日,很少吃到蔬菜及干饭,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更不用说肉及油脂类的食物了。教学设备一直极差,且多要由教师自备。几乎所有的学校除有一两间茅草房及黑板、课桌凳外,就“余则四壁”。
民国时期,怒族的学校规模都非常小。在校生注册人数最多的也不足百人,一般学校在校生的注册人数都仅在一二十人左右,实际上,经常到校上课的学生多则一二十人,少则三四人,民族教育状况可想而知 [③]。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教育
解放后,怒族的教育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及关怀之下,发展很快。从整体上看,怒族的学校教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怒族学校教育的改造、起步及初步发展时期(1949—1956年):1949年6月后,怒族地区的各县相继和平解放,政府接管了福贡、碧江两县的十多所学校(贡山县原有的4所小学早于1948年前后停办,校产被一抢而光!)。1950年初,福贡、碧江两县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指示,在“调整、统一、整顿、巩固”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对旧学校进行了改造。贡山县第一任县长和耕则在一无教师,二无校舍的情况下,于1950年4月指派了两名干部在原省立贡山小学的旧址上复建了一所初级小学。为了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发展边疆建设事业”的步伐,丽江地区行署于1950年开始,每年都要向贡山、福贡、碧江等县派来两批教师。怒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在政府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的发展。1955年9月15日,怒江州设在亚谷的第一所中学招收到了20多名初中生从而结束了怒地没有中学的历史。
到1956年底,仅福贡、贡山两县就建起了49所小学,在校生达3500多人,其中,怒族学生由1949年的71人发展到近700人。
怒族学校教育在狂热、调整过程中的发展时期(1957—1965):1957年7月,怒江州为了推行“双语双文”教学,将全县的小学教师都集中到碧江学习新傈僳文。紧接着“反右倾”、“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所有的教师又被迫留在州府搞运动。这次运动及学习持续的时间近一年之久,其间所有的学校停课,数十名教师遭到了批斗、开除公职、拘留及劳教的处理。“运动”刚一结束,教师们返校复课不久,“大跃进”的狂风又席卷而来。受其影响,怒江也打出了“苦战三个月,完成全年教学任务!”的口号。很多学校的学生仅用二三个月的时间“学完”了一年的课程,一经检查,学生则一无所获!为了适应妇女在“大跃进”中的需要,怒江的第一所托幼所于1958年在贡山创立(福贡县的第一所幼儿园则是在1965年才建成)。当年,学校教育发展迅猛,仅福贡、贡山两县就有62所小学,在校生4629人,其中怒族学生就达800多人。地方政府因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所有的学校均走上了“以劳代教”的道路。学校每天都要花一半左右的时间去搞生产劳动,高年级的学生还要参与“人人扫盲”的运动。教学质量因此而直线下降。加之,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将各县的家底吃空了,全州处于饥饿状态。不少迫于生计的学生随家长外逃,辍学率极高。到1961年,学校虽增至67所,教职工增至176人,在校生则下降到2406人。1962年,福贡、贡山两县只好将学校调整为55所,在校生继续下降为1535人。1964年,国家加大了教育的投资力度,地方又开始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到1965年时的办学形式很多(有耕读小学、早晚班、半日制、隔日制、轮回制、工读学校等),学校数量猛增至127所,在校生为3795人。乘“大跃进”的东风,政府于1958年还在福贡、贡山两地各建起了一所中学(实系附设初中,这两所附中直到1965年也未独立)。附设中学的建立,结束了贡山等地的中学生要背箩负囊走七八天的路去碧江(当时的州府)上学的历史。
怒族学校教育超常发展时期(1966—1976年):1966年7月至1967年春,全州的中学教师集中到丽江专区、小学教师集中到怒江州府搞“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学校停课,直至次年4月才又“复课闹革命’。“文革”初期,教师被污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老师斗老师的运动常常开展。碧江中学被当成“修正主义的旧学校”,其科学馆因此被劫,图书资料被偷窃焚烧,70%左右的老师被赶到“五·七”干校劳改,成绩卓著,名重一时的碧江中学于1968年被“革委会”撤销。1968年后,学校的领导权交给了“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接着中央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中学因此而一律停办,“军管会”甚至还强令“高小生”也要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致使学校教育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1969年,开始贯彻中央1968年的“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的指示,仅这年内,贡山、福贡两县的学校又由原来的131所增至235所,在校生由3400人增至4799人;教师由186人增至317人。1972年,又遵照云南省教育革命委员会关于要在“四·五”期间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指示精神,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促成学校在数量上高速发展。到1976年时,在总人口只有六七万人的福贡、贡山两县就建起了312所小学,在校生人数达9474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高达90%以上!从表面上看虽然实现了“读小学不出村、读高小不出大队、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中不出县”的目标。然而,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怒江的客观实际,给学校的实质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如因教师严重不足,只好将一些仅具高小水平的人也招来当教师。为了实现“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中不出县”的目标,福贡、贡山两县均在还不具备条件的各区中心完小内办起了附设初中班。1970年7月,停办了一年多的福贡初级中学恢复招生,贡山县初级中学则因招了个高中班而变成了完中。到1976年时,福贡、贡山两县就办起了12所中学(含附中),有在校生1597人。此外,怒江州还在“文革”期办起了一所师范、一所农校及一所卫校。
怒族学校教育健康发展时期(1977—2010年):“文革”结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间,因“左”的思想及“两个凡是”的错误还未得到全面纠正,中央还提出了要在“五·五”期间普及初等教育的要求。受此影响,怒族地区的学校仍在走“高指标、大发展”的盲目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怒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才开始逐步地全面地走上了“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健康发展之路。根据怒江实际,政府对怒地的教育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怒族的教育结构与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水平基本相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州教育战线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怒江的民族教育事业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教育成果十分显著。
从1981年到1993年的13年里,全州一共投资5600多万元(含群众集资、投工献料等1200万元)国家投资的教育事业费也从1981年的518.2万元增加到1993年的2853.7万元,增长了4.5倍。1986年—1996年,怒江的教育支出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逐年有所提高。1986年全州教育支出1328万元,占全州财政支出6751万元的19.6%,发展到1995年全州教育支出为5337万元,占全全州财政支出32101万元的23.2%.教育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1986年全州小学1082所,学校占地面积1812亩,校舍建筑面积为250057平方米。普通中学26所,学校占地面积554亩,校舍建筑面积为80479平方米。到1996年,又共有小学1192所,学校占地面积2408亩,校舍建筑面积为337277平方米。普通中学25所,学校占地面积944亩,校舍建筑面积为148915平方米。
总之,全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初具规模,形成了以基础教育为中心,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民族教育体系。到1993年全州共兴办中等师范学校1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3所、完全中学7所、初级中学17所、农职中学3所、小学1131所、幼儿园16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8.03%,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74329人,占全州人口的16.64%。教职工人数达4578人。
1998年底,全州各类学校又发展到1250所,在校生总计达79150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90%以上。2004年全州普通中学在校生为24372人,小学在校生48936人,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共计79947人,是1954年的26.7倍。及至2005年,怒江州拥有中等专业学校1所,完全中学8所,职业高中2所,小学1080所,幼儿园17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25%,各级各类在校生81177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达75381人,占全州在校生人数的92.86%。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使怒江州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学校教育普及到了村村寨寨,广大怒族的适龄儿童和全国少年儿童一样享受着全民义务教育。为了解决民族学生的实际困难,确保他们安心读书,党和政府还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对小学和中学全部实行助学金制度,并从1980年起开始建立寄宿制中学和小学。
此外,自恢复高考以来,全州每年都要输送少数民族学生到省级以上的中等专业学校和大专院校深造学习,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技术特点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他们成了怒江州各项事业发展的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全州被省内外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录取的学生分别是46人和428人。1986年全州被省内外大专院校录取的又有162人,省内外中专学校录取426人。到1997年全州被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录取的分别墅增至168人和607人。其中,怒族大中专学生的入学率也逐年递增,1995年被大专院校录取的有5人,1996年为2人,1997年为3人,1998年10人,1999年10人,2000年为9人,2008年12人,2009年15人。如今,在怒江州的各行各业里都有了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为民族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④]。
第二节 民族文学创作
新中国建立后,怒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进程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怒族社会和怒族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然而,相对依然封闭的环境和依然贫困的生活,再加上存在着浓重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无处不在的鬼神观念)的阴影,致使怒族人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是那么步履维艰,直至跨入21世纪的今天,绝大多数怒族同胞,仍然没有脱离贫困的生活。建国30多年,到了80年代中期,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怒族当代文学,开始起步。
建国以来,怒族社会和怒族文化跃进式的巨变,严格说主要来自于外在因素(外力)的牵引和推动,以及外在环境的改变。因而,这种变化,或者说这种进步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过程。在经历了新生的喜悦之后,接踵而来便难以避免地出现和产生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以及文化演进过程的反复,心灵与行为的矛盾,文化内核与文化表层的相悖等现象。生活在这种社会现状下的怒族作者,便以文学的语言对这一切作出描述或者探究,从而构成了当代怒族文学反思性的主题。
随着教育的发展及提高、汉语文的普及、交流的扩大、观念的转变以及各级党政部门的提倡与培养,在怒族中间,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党政领导、科技干部和教师、医生,还涌现出一批批文艺工作者,出现了本民族的作家群。他们著书立说,创作小说、诗歌,改编音乐,设计舞蹈,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发掘怒族文化的深厚内涵,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催生了怒族文化艺术的“春天”。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经过广大怒族文化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和辛勤耕耘,使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得到了挖掘和整理,并出版发行了《怒族民间故事》、《怒族独龙族民间故事选》,使口头文学变成了书面文学。这些故事情节生动,伦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再现了古代怒族人民同大自然和社会邪恶势力斗争的英雄事迹,歌颂了他们创世立业、开拓边疆的聪明才智和美好的情操,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叶,怒族作家彭兆清发表了《啊,那遥远的山泉小学》。此系怒族人士首次用汉文撰写小说,该小说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其创作的小说《女岩神祭》获《边疆文学》奖。叶世富创作的散文《梦想不到的事情》、彭兆清散文《“吝啬鬼”大叔》分别荣获云南省少数民族创作奖和《云南日报》桂花杯散文征文奖。和光益的通讯《与冰心相识在北京》荣获《人民日报》社等单位举办的第五届新世纪之声《中华颂声》征文活动银质奖……
此后,怒族创作人员不断涌现,先后在《怒江》、《民族文化》、《边疆文学》、《大西南文学》及《云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及诗歌,出版个人专集;《怒江人文地理杂志》(由《怒江》改名)等杂志也积极刊载怒族作家的作品,各方面的互动,促进并繁荣了怒族的文学创作,带动文艺事业的发展。当前,在怒族之中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作家群,作品数量逐年增多,凸显特色,影响不断扩大,成为了当前怒族文化艺术中的突出亮点。
从50年****始,有关部门组织怒族学者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专家学者,辛勤努力,跋山涉水,普查文化资源,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神话及民间歌谣,整理加工,印刷出版,向世人展现了长期被掩盖的怒族丰富文化宝藏。如李卫才、叶世富、彭兆清等人辛苦努力,搜集和发掘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龙女故事、孤儿故事、爱情生活故事等,整理并出版了《猎神歌》(木玉璋)、《创世纪》(彭兆清)、《怒族民间故事》(叶世富、郭鸿才)、《婚礼歌》(叶世富)、《怒族独龙族民间故事选》(左玉堂)、《种竹歌》(李卫才)、《祭猎神调》(赵鉴新)等。叶世富等编撰了《福贡民族民间文学集成》、《贡山民族民间文学集成》等。这些作品汇集了怒族民众的丰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长诗短歌、童话及寓言等,承载了怒族民众的丰富知识、活跃的想像及聪明的壑智,实现了口头传说到书面文字的转化,为认识及研究丰富、绚丽的怒族文化提供了素材,促成了《怒族文学史》(左玉堂)的梳理及撰写,使藏在深山的怒族文学艺术走出怒江,走向云南、走向全国。
其间,李卫才、段伶还搜集整理了《山神娶妻》、《乍付赛与乍付玛》等百余首怒族民歌,编辑出版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碧江怒族卷》。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发掘及吸取怒族音乐的特殊元素,创作了诸如《弹歌要在大风里弹》、《美丽的声音》、《怒江在欢唱》、《怒家寨里喜事多》、《小弩弓三尺三》等200余首富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色的歌曲,与时俱进,丰富了怒族民歌的表现内容。这些歌曲不仅在怒江州、云南省产生了较大影响,还唱响了全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其中《怒江在欢唱》(段伶作词)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受到了积极的评价;由李卫才同志以“达比亚”乐曲为基调创作的《歌声飞出心窝窝》成为了六七十年代流行全国的怒族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此制成唱片,向海内外广播。该歌曲荣获国务院文化组的创作奖,被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入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歌集《占地新歌·续集》。
近年来,怒江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搜集整理了一批怒族民间舞蹈,发掘民族文化内涵,结合时代特点,加以改编,注入新的音乐元素,表现特色,先后推出《斗羊舞》、《双人琵琶舞》、《反弹琵琶舞》、《蝴蝶舞》等,在省、州历次文艺汇演中,屡获嘉奖。
怒族作家彭兆清(现任怒江州政协副主席)长期坚持创作,笔耕不辍,近年来公开出版了《流动的驿站》、《七彩仙境》、《灵性的土地》等三部散文集,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大批介绍、总结怒族文化艺术和从各个角度研究怒族问题的专著相继问世,如杨元吉用文字记载了丰富的怒族音乐元素,撰写并出版《怒族音乐史》,生动描叙了怒族千余年音乐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怒族音乐的主要内涵及特色所在。由刘达成、李绍恩担任主编、副主编的《怒族文化大观》、陶天麟撰写的《怒族文化史》等著作的出版发行,较全面地介绍了怒族的历史、文化与习俗,对怒族丰富而灿烂的文化作了系统的总结。李绍恩、何淑涛等人分别撰写了《云南少数民族妇女——怒族》、《复苏了的神话·怒族》等著作。
其间,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等出版了怒族支系语言《柔若语研究》,李卫才、段伶、李绍恩、李志恩等人也在记录、整理、分析怒苏及若柔语的基础上公开出版了《怒族·怒苏语言资料集》、《怒族·若柔语言资料集》等著作,对怒族语言内涵及特点的认识推至具体化、精细化,对于分析及保存怒族的各支系语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些语言书籍通过怒族语料的分析、研究,收集和保存了怒族民间的祭词、古歌、神话、传说、童谣、故事、寓言、谚语。随后,秦和平、徐整运等承担修订编写的《怒族简史》、李月英的《“三江并流”区的怒族人家》、攸延春的《怒族文学简史》、赵沛曦、张波的《怒族历史与文化》,何林的《阿怒人》以及怒江州政协文史委编撰的怒江州民族文史资料丛书《怒族》、福贡县统战部和匹河怒族乡人民政府牵头,曲路主编的《歌声飞出心窝窝——李卫才歌曲选》等专著公开出版发行。此外,还有一大批研究怒族问题的专著也陆续问世(内部出版)。为从多方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怒语及怒族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大家站在不同层面介绍了怒族,从不同视角宣传了怒族,使外部世界认识了怒江,认识了怒族。
在此期间,还有怒族作者创作的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见诸于各种期刊、杂志。
第三节 民族艺术创新
怒族也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的宝贵文化艺术遗产,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怒族地区的原生态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辅相成,民族艺术不断创新和发展,放射出璀灿的光芒。
(一)民歌(即叙事歌)
怒族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歌。怒族民歌分为两类:一种是“火塘边坐唱”歌,一种是结婚歌(或婚礼歌),还有即兴唱的诗歌,但为数不多。至今仍在怒族人民中流行的有《火塘边坐唱》、《结婚歌》或《婚礼歌》、《若登调》、《邓邓夺》,还有带有宗教色彩和富有民族特点的古朴的《祭猎神调》、《瘟神歌》和各种祭祀歌等数十种。
怒族的这些民间文学,代代相传,口耳相授,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前,怒族的文艺受到摧残,谈不上挖掘和整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民歌,在此基础上,还创作了很多富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民间歌曲和舞蹈,使怒族文艺得到了新的发展。由怒族音乐工作者创作的《怒江在歌唱》,首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并获奖。同时还创作了很多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舞怒族新生活的歌曲。其中,用怒族声乐素材创作、驰名中外、在群众中流传甚广的《歌声飞出心窝窝》已被中央、省广播电台录制成唱片并列为对外广播节目,深受群众的欢迎。
(二)舞蹈
怒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民族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大都反映生产生活,有摹拟动物声音、形态的,有反映搬迁寻找土地开荒播种的,有反映男女爱情生活以及打猎等生产活动的。有音乐伴奏的主要有《第一次找土地》、《古战舞》、《双人琵琶舞》、《欠吾舞》、《打猎舞》、《婚礼舞》、《祭鬼舞》、《山乌炭渣》、《青线舞》、《割小米舞》、《交租舞》、《猪神舞》、《怀念舞》、《我看你,你看我》、《阿楼西杯调》、《戏几沃》等,共120多种。舞蹈形式有自弹(自吹)自舞的集体舞,动作粗犷敏捷,深刻细腻,旋律奔放有力,节奏鲜明,具有古朴豪放的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近年来,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怒族民间舞蹈有了新的发展,先后推出了《斗羊舞》、《双人琵琶舞》、《反弹琵琶舞》、《欠吾舞》、《怒族姑娘》、《蝴蝶舞》等,并参加了省州县三级文艺汇演。其中,用本民族素材创作的《双人琵琶舞》、《反弹琵琶舞》、《斗羊舞》等先后获奖。
(三)器乐
“达比亚”弹唱家阿迪·范进良将“达比亚”弹唱《哦得得》在整理基础上,注入时代元素,加以改编,展现新风格,分别参加了“95上海中国民族风”及“1995年云南春节联欢会”的演出,受观众的广泛好评。此后,他应邀唱到了香港,唱到了台湾。
(四)绘画
怒族先民留下的托坪吴府岩画和腊斯底壁画早已远近闻名,极具考古和文化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怒族的绘画人才层出不穷。怒族画家、原怒江州文化局局长李文华与人合作的《颂歌飞出心窝窝》曾在1976年西南四省少数民族画展上受到好评;原福贡县匹河文化站付大山同志创作的木刻《出诊》,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画展并荣获一等奖。此外,许多怒族绘画作者在《民族画报》、《春城晚报》、《怒江报》、《怒江》等报纸、期刊、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五)影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怒族为题材或与怒族有关的影视作品,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反映了怒族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如1978年云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怒族的传说》,以及1992年辽宁电视台摄制的纪实片《怒族一家人》以及电视剧《如歌的响铃》和怒语译制片《国际大营救》等等。
(五)摄影
2007年7月,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怒族青年摄影家李绍智的历史文化摄影作品集《兔峨土司衙署印象》。
第四节 民族社团活动
为了促进怒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怒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宣传与弘扬怒族文化,怒族民间社团—怒族学会于2003年成立,成为云南民族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之一,创办并发行了《怒族研究》会刊。随后,福贡、贡山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本县的怒族学会。目前,兰坪、泸水两县也正筹备成立怒族学会。
云南民族学会怒族专业委员会,简称怒族学会,于2003年12月24日在怒江州州府六库成立,现为第二届。
(一)主要工作
1、组织本会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引导会员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正确发挥专业委员会的向导作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研究能力。
2、广泛搜集、整理怒族的历史文化典籍和各种资料,编辑出版研究成果和资料,向各级党政部门推荐研究成果,供领导机关决策参考。
3、通过广泛团结国内外的一切有关学者和社会团体,抢救、保护、发掘、弘扬怒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组织和规划有关调查、研究、讨论会及参观、考察活动。
4、协助组织怒族的主要节日活动。
5、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努力扩大怒族与外界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活动。
(二)主要学术活动
学会成立以来,本会领导和本族学者先后参加了“四江流域傣族文化”研讨会、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学术、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省民族学会工作研讨会等学术活动。
学会定期出版会刊《怒族研究》,以抢救、发掘、弘扬怒族传统文化为宗旨,开辟多个专栏,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和会员开展怒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编撰了《怒族研究》、《怒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集》、《怒江州民族文史资料丛书》(怒族卷)、《怒族人物》、《甲怒良苏怒语》等书籍和文献资料;摄制、制作了《怒族传统文化实录》、《怒族民间文化资料》等6套光碟;建立了网站《怒族人民信息港》,并在福贡、贡山成立了怒族学会分会;积极筹建“怒族文化生态村”。
(三)其它活动
积极组织开展怒族传统节日活动;派员协助参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团体对怒江、怒族的考察研究活动;参与了有关企业在怒江开发资源的协调、配合工作;积极参与配合、协调有利有益于学会工作的各种调研活动和联谊活动。
此外,随着怒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许多怒族乡镇、村寨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同样对于怒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组织、协调、纽带和宣传作用。
第五节 民族创意产业
怒族居住的怒江目前还相对落后,但大自然赋予了怒江无限的宝藏和绝世的美景,这里多民族和谐相处,多宗教和谐共存,多生态和谐共生,被誉为“自然地貌博物馆、生物物种基因库、人类文明处女地、民族文化大观园”,是目前全省乃至全国原生态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全州各族干部群众面向大环境、把握大机遇,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完善发展思路,强化发展措施,积极探索和实践建设民族文化强省,旅游“二次创业”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途径,确立了“三基地、一品牌”战略目标,把民族文化作为怒江大峡谷的灵魂,把生物多样性作为怒江大峡谷的生命,把多元民族文化及生物多样性基地建设作为承载怒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其中,将民族文化资源与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转换和价值增值的重要途径。以民族文化创意为先导,打造从产品、服务乃至生态复原、文化复兴的多层次产业链,实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尚的对接,在发展中传承。
近年来,怒族干部群众借助其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紧扣民族文化元素,倾力创新开发,大力打造文化创意品牌,并开始走向国内、国际市场。如今,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发展,民族传统工艺文化产品不断创新,推动怒族地区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当前,怒族的民族创意产业主要体现在民族服饰生产、工艺品生产、特色饮食、文艺演出、举办传统节日等方面。
怒族服饰产业:怒族的怒毯即古书中的“红纹麻布”, 色彩鲜艳,耐磨结实,美观大方,既是当年怒族上贡土司的贡品,也是他们对外交换的主要商品。解放后,怒毯又采用棉线、晴纶线及开司米等为原料进行纺织,质地更为轻柔,色彩越显明丽,图案愈加丰富,是怒族同胞家里的陈设用品和馈赠佳品。现在,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怒毯的纺织、生产、销售已成为怒族地区的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行销海内外。
此外,州、县都有民族服装厂生产怒族服装、怒族花挎包等产品,深受中外游客青睐。
怒族饮食产业:怒族有着独具特色的传统饮食文化,如“狭拉”、漆油鸡、手抓饭、瑟琶肉、石板粑粑、杵酒、漆油茶等,以其原生态的文化底蕴,不仅在当地很有知名度,深受人们喜爱,有的还成为州里、省里知名的特色饮食品牌,倍受推崇。
民族工艺品产业:怒族的民族工艺品如弩弓、弩箭,民间乐器“迪里土”,怒族陶器,怒族的各种手工编织竹器,如簸箕、背篓、摇篮、筛子等等,也越来越成为远近闻名,深受人们喜爱的产品。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怒族民族工艺产业年产值都在200万元以上。
文艺演出:随着怒族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文化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依托怒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开展文化创意产业有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如福贡的“沙滩埋情人”、“哦得得歌舞表演队”、
举办传统节庆活动:近几年来,怒族学会精心组织、策划,在省里和州县上认真筹办好怒族的重大传统节日欢庆活动,如贡山的“乃仍”、福贡的“如密期”、兰坪的“周登走”等节庆活动,并努力将三个怒族集聚地区的三个传统节日逐步统一起来。这些庆祝活动,既展示了独具一格的怒族传统文化和节日,又传承、弘扬了怒族文化,对进一步传承、弘扬、挖掘怒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以开展怒族传统节日为契机,积极推动民族地区商贸、旅游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目前,福贡县匹河乡老母登村、贡山丙中洛乡的民族生态村和兰坪兔峨乡的怒族古歌擂台赛等民族文化创意项目都在积极筹划当中。
总的来说,当前怒族的民族创意产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带动了当地公交、宾馆、饮食、娱乐、商品零售业的增长,带动了其他项目的升值,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前景十分广阔。
第六节 民族文化价值
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族群或民族所创造、拥有的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可以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经验和行为模式的总和。
恩格斯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
民族文化具有多重的价值。民族文化对各民族来说,首先,它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知识、工具及手段和方法,也是民族社会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它具有民族生存、发展的实用价值和功能;其次,民族文化又是各民族的精神财富,它包含着各民族特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
民族精神是民族思想观念和精神性格的载体。民族精神主要是民族文化精神,它存在于民族文化的物质和行为(制度)模式之中,通过物质和行为得以体现。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思想观念和精神的载体,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民族精神始终贯穿于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从共时性看,民族精神贯穿在民族文化的各个种类、方面和民族文化存在的各个地方。无论是民族文化的整体中,还是在民族宗教、道德、艺术、风俗、法律等各亚文化中都渗透着民族精神,哪里有民族文化哪里就有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存在的地方就有中华民族精神 [⑤]。 怒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怒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开发和保卫了祖国的边疆,不断地总结与自然和社会抗争的经验,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文化体系。怒族文化多元,地区各异,精彩纷呈,特色鲜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位置和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怒江地区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世界罕见,构成了三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并流)地区最有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宝贵资源。从民族和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怒江地处内地中原文化、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青藏高原文化的边缘地带,这里生活着12个少数民族,其中6个少数民族为当地独有。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之间所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差异很大,极不平衡,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人类社会发展经过的几种历史形态都有存在,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之自然资源又较为丰富,很容易形成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由此获得了一种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样,无论从该区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总体而言,或是从某一个民族的文化因子来看,其文化形态都较少发生重大变革,更少出现文化断层而保存良好。从怒江区域少数民族文化史中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如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口传文化、节日文化、居室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交通文化等中,人们可以看到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基因库的存在。正是由于该区民族文化环境及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因而被学术界誉为“多民族走廊”,称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基因库”。
全球化时期,由于文化经济的出现,文化的经济属性日益明显,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具有了审美意义和价值。传承怒族文化,就是找出怒族的文化特色和最有价值的特殊文化遗产,深入研究文化现状,制定保护和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培养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产业化发展,提高民族文化竞争力,最终使怒族通过自己的文化获益。
参考资料:
[1]《怒族文化史》,陶天麟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怒族文学简史》,攸延春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3]《怒族历史与文化》,赵沛曦,张波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4]《怒族研究》,2008总第四期;
[5]《云南民族概要》,王四代,王子华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①] 段伶著:《怒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②] 陶天麟:《怒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③] 陶天麟:《怒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293页。
[④] 张 波:《怒族文化与历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⑤] 王子华:《云南民族概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